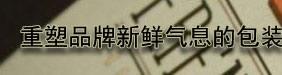從“標志性建筑”到吸引人的公共場所
作者:弗雷德·肯特 來源:333cn.com 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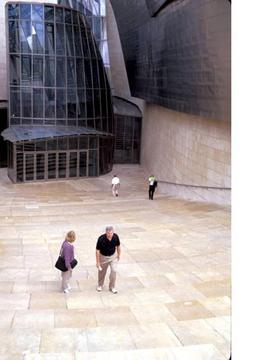
圖2、3、空曠的畢爾巴鄂博物館。
蓋里的畢爾巴鄂博物館在1997年向公眾開放時,作了一個權威性的設計聲明,成為畢爾巴鄂著名的當代文化設施之一。但媒體的宣傳只有很短的生命力。為了有持久的影響力,一個地方必須不斷地改造自身,做到與時俱進。這個具有開創性的博物館的下一步,將是使它發展成一個突出的地方,不僅是以它們的建筑和藝術品,讓更多的人來參觀或體驗。
它需要成為這樣一個地點。人們自然地希望來游玩,以享受這里全部的體驗和一個令人驚奇的城市的活力。我們的評價是,畢爾巴鄂博物館沒有做到這一點。我們將它作為一個藝術品來贊揚,而不是作為一個吸引人的地點來贊揚。
設計師為何害怕不是他們的同類的人的評判。
我是蓋里的某些建筑的狂熱愛好者。我認為芝加哥的“千年公園”(Millennium Park)的普利茲克露天音樂廳(Pritzker Pavilion)是杰出的,是一個真正的標志性建筑。音樂廳的舞臺、擴大良好的聲音系統的、穿過一片巨大的草地和座位區的“格子棚”,真是太棒了!我認為這是蓋里的最精細的作品。
然而,標志性建筑的最大優點之一——這些新的和有時極好的建筑的令人注意的品質,在設計師、客戶和惟一的興趣是創造有吸引力的“紀念碑”的建筑推進人的手中,成為它的最大的缺點。

圖2、3、空曠的畢爾巴鄂博物館。
太少的考慮是,在人們首次參觀之后,讓這些地方繼續吸引人們。由于這些建筑有許多是文化機構,它們的成功依靠灌輸一種公眾意識和它們的參觀者之間的聯系,但這是一種特別短視的戰略。以前的參觀者不會支付這些建筑物的各種開支和維護費用的賬單。
蓋里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3幢建筑物,顯示了沒有背景的建筑怎樣留下讓人驚奇的東西。杜塞爾多夫感到驕傲,他們增加了名氣,是他們,而不是上海,獲得了蓋里給他們的城市的祝福。但我們去參觀蓋里的作品,可能看到的也是門可羅雀的景象。
城市作為標志性建筑的“明星建筑師”和他們的資助人和欣賞他們的新聞記者想象物,是脫離普通市民對他們的社區的想象的世界。這就有助于解釋:今天的設計師為何很害怕不是他們的同類的任何人的評判。
我很清楚地記得今年夏天在“阿斯本理念節”(Aspen Ideas Festival)的情況,當時,我問弗蘭克·蓋里一個有禮貌的但直率的問題:為什么杰出的標志性建筑很少成為吸引人的公共場所。
蓋里拒絕回答這個問題,并且揮手讓我離開。這是一種傲慢的表現,知名新聞記者詹姆斯·法羅斯(James Fallows)將其與路易十四相比。
這次大會的主持人托馬斯·普利茲克(Thomas Pritzker)——普利茲克獎評審團的主席——也避開這個問題。一些人聽到這種提問之后鼓掌,他示意我坐下,然后這個年青的建筑師走到我的面前,對我說,我是大膽的、令人驚奇的。我認為我只是問了一個關于背景和場所的簡單問題,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,不需要多動腦筋。
我認為,這個簡單的問題,就應當由每一個設計師和每一個客戶提出來:“我們將用什么來保證設計和創造良好的公共空間,讓人們使用和享受?”總的說來,一個設計師避開這個問題,給這個職業和團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。好的設計的內涵,比進行“大膽的”、“創新的”美學表達要豐富得多。優秀的設計,應當幫助我們解決今天的世界遇到的重大的城市問題——從環境破壞到經濟衰退——到社會異化。當建筑師集中他們的全部才能于設計工作,用以制定他們最新的藝術聲明的時候,建筑遠未達到它的潛力。
繼續閱讀:
下一篇:建筑水體景觀設計發展前景
上一篇:美國:中國無須將時間浪費在創新上
編輯:shx
推薦
花邊
排行
專題
平面設計
工業設計
CG插畫
UI交互
室內設計
建筑環境
中國設計之窗 © 版權所有 粵ICP備09030610號
Tel:0755-21041837 客服:serve@333cn.com 資訊提交:news@333cn.com
Tel:0755-21041837 客服:serve@333cn.com 資訊提交:news@333cn.com